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陕工网(029-87344649)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陕工网(029-87344649)
贾平凹在工作室接受专访 杨小兵 摄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代文学大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在2020年第三期《当代》杂志推出后,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社会层面,犹如平静的湖面涌起阵阵涟漪,闪烁出绚丽的光彩,好评如潮,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学又一巨著。《暂坐》以现代城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一群中年女性在追求经济独立、个性解放、精神自由以及理想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困境中所展现出的复杂人性。小说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近日,笔者专访了贾平凹。
笔者:贾老师,您好!您的新著《暂坐》,是您的第十八部长篇小说。您在后记里说,这部小说是您70岁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可见您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这部描写女性群体形象的小说,是您小说创作题材中不曾出现的“新变化”“新面貌”,您的创作思想是什么呢?
贾平凹:《暂坐》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长篇《酱豆》的初稿,先修改整理出了《暂坐》,然后再修改整理出了《酱豆》。《暂坐》在《当代》杂志推出后,七八月份,两本书将同时出版单行本。到了这般年纪,写作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写自己长久以来想写又没有写的东西。谈不上什么“新变化”“新面貌”,只是像水流着,流到哪儿是哪儿,因往下流的地势不同,流量不同,呈现的状态、颜色、声响越不同而已。
笔者:您之前的长篇小说作品多以乡土题材为主,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您的笔触深入到现代城市生活,而且通过这十多位美丽优雅而又各自有一段难以言说的伤痛个人史的女性人物,构成了生动鲜活的“西京”生活故事,这是您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一个新的突破,您能讲讲创作这部小说的心理动因吗?
贾平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说,不了解农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我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乡土的,写近百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现在城乡的概念进一步模糊,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农民和市民无法分清,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文学当随时代、社会,文学自然也要变化。我在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应该写写城市生活。其实也写了许多城市题材的作品,除过大量散文外,小说也不少,比如《废都》《白夜》《土门》《高兴》,但还都是写乡下人进了城的故事,而《暂坐》中虽也有从乡下进城的人物,大多已经是完全的城市人了,过的是真正的城市人的生活了。
笔者:《暂坐》的创作背景很是贴近时代,您准确而深刻且艺术地反映了当下正在演进中的历史生活,这十多个女性形象非常鲜活而生动,您能讲讲您的艺术原型吗?
贾平凹:小说都是有原型的,但原型在小说写作中仅起到一种诱发写作的冲动和写作的切入,写作起来了就无关于原型。《暂坐》里的那些女子,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的一群女性形象,这我在后记里已详细说过。不仅那些女子的故事,还有所在城市的街巷,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小说是不能对号入座的,一对号入座就荒唐和尴尬了。发现和表现灵魂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才是小说的精髓。
笔者:《暂坐》采用了“人物+地点”这样的“短片”局部写法,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长片”完整风貌,这样的笔法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和立体,是一种艺术上的新突破,能谈谈您的艺术心得吗?
贾平凹:小说是怎么写都可以的,尤其现代小说。建筑因地势而赋形,小说以内容决定形式么。《暂坐》是写群像的,又是写日常的,采用“人物+地点”的写法,宜于更好地表现人物,又宜于节奏的紧凑,还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
笔者:在长篇小说《暂坐》里,您采用散文化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古典小说韵味,体现了您的审美追求。散文化的小说表现手法,在您的笔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您是如何结构这部小说的,这样的结构艺术难度和优势在什么地方?
贾平凹:《暂坐》里人物众多,又没有离奇的故事,仅仅有个轮换去医院照顾夏自花的线索,那么,为了写好人物,就得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注重这些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和表情,这样才能使小说好看。而大量的市井描写,生活的智慧性的感悟则弥漫和充盈其间,才能使小说有一种韵味。为了结构的需要,其中冯迎的死亡、迎接“活佛”,等等,都是有其讲究的。
笔者:在《暂坐》里,您塑造了俄罗斯女性“伊娃”的形象,并通过她的“眼睛”来打量当下社会生活、勾连起整个女性形象,通过这个带有“陌生”和“外来者”视角的“伊娃”,您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贾平凹:伊娃的角色是小说结构的需要。伊娃的视角其实就是作者的视角。采用“外来者”或“跳出来”的视角,这样更容易表现作者的一些企图:小说并不是仅仅写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还应有生活的智和慧。试想,我们在阅读任何一部小说,是不是从中想受到一些思想的精神的启示和感悟、一些生活的智和慧呢?我读小说,就是这样读的,如果其中没有那些思想的精神的启示和对生活的智与慧的感悟,那有些可摘可抄的好句子也行么。否则,就把所读的书扔了。
笔者:您在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婚姻与爱情的实质不单单是情感,而最重要的是生存的条件,没有生存的条件,爱情就无法附丽,您的这句话是在表达这层含义吗?
贾平凹: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之所以用在此,也是表达当下的一些婚姻爱情的实况。世上或许有纯真的爱情吧,但现在的社会里更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使走在一起了,也多是“饿着”,“吃了饭”便各走各的。正如此,《暂坐》里的女子追求经济独立,要自我,要自由,要时尚,要潇洒,要文艺范儿,才多是未婚或离婚后的单身。这是别一样的时代,这也是别一样时代里的一群别一样的女子。
笔者:《暂坐》后记里引用了一段古文,“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土垣,垣外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您说“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这句话是否说,当下社会的女性生存与精神状态处在双重的矛盾之中,一是她们各自喷吐着芳华的娇娆,二是她们又处在艰难的困苦之中?
贾平凹:你说得对。《暂坐》中的女子是一群别样的小团伙,她们在美丽着奋进着,同时在凋零着困顿着。我说过,风吹风也累,花开花亦疼。这群人代表着城市的时尚,犹如道边的树,是美的风景,能标示着风向,但大风来了会断枝折股,即便是微风,那叶子也在不停地摇晃翻动。
笔者:世界如若老子所说是“混沌”的,那么,“混沌”的世界里“清水出芙蓉”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和情感上,或者是身体上,都担负着比常人或者男性更为沉重的东西,这些沉重的东西,构成了您笔下这十多个女性摇曳的姿容和难以言说的苦痛,这就是女性的两难吗?
贾平凹:是呀,这也是我最初想写《暂坐》的原因。这群人看似光鲜,其实辛酸;表面看似热热闹闹,却每个人都很孤独。
笔者:《暂坐》与您的《秦腔》《山本》等长篇小说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手法上,走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您关注女性命运和女性生存,全然展示出一个新时代作家的风貌。可以说,这部小说勘破了当下社会女性精神与生存的真实状况,必将是您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您怎么认为?
贾平凹:也不敢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可能在以后会继续写些关于城市生活的作品。我读过一篇文章,里边写道:“城市越是现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越是艰难,其惶然命运的无望,失去信仰的撑持,远离存在的意义,彼此相交集,各自成障碍,表面常来往,实际不兼容,每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个人又身处边缘,不见外表的冲突,却在群体中大感不适,既虚弱又脆弱,既无力又无奈,既有所萦怀又无动于衷,情感的损伤无法疗治,精神的苍白难于慰藉。”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笔者: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您的这部长篇小说,既反映了这个时代昂扬奋进的主流气象,也揭示了这个时代腐朽的“坏”的一面,尤其是您的笔下被“双规”的领导,为当代文学奉献出一个“新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贾平凹:那个被“双规”的领导,为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事情,连同所描写的雾霾,以及所有的市井现象,都是那些女子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背景。因为那群女子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追求故事为什么发生,从而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
笔者:除过小说的后记,您还想对广大读者说点什么呢?
贾平凹:有的书宜于快读,有的书宜于慢读,如果读《暂坐》,还是慢慢读着为好。 □柏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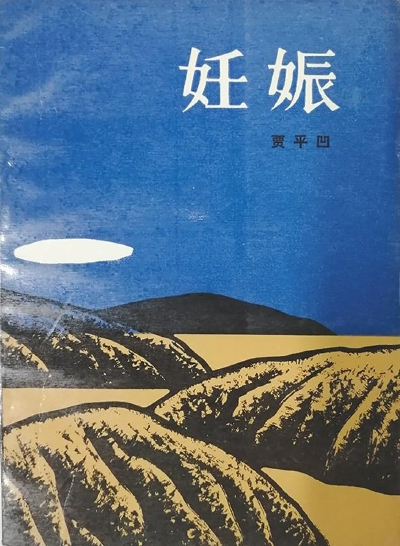
1988年

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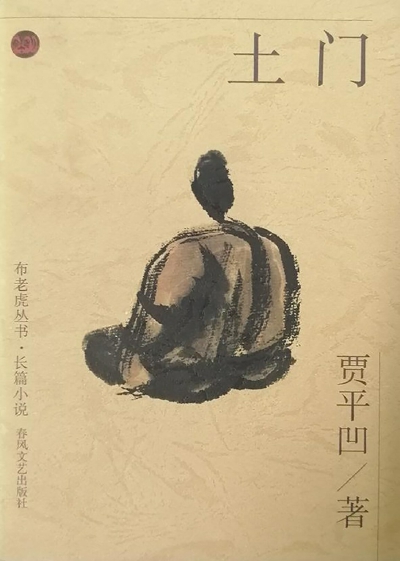
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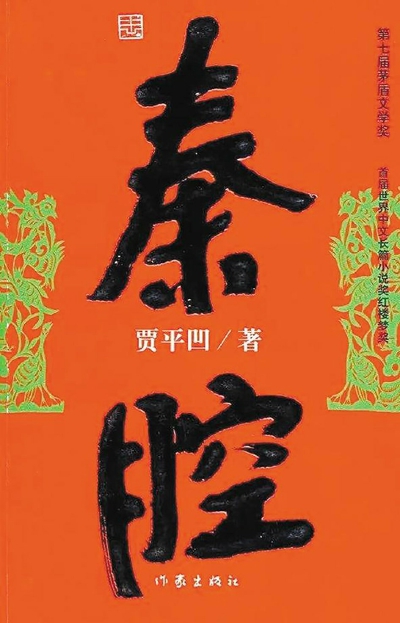
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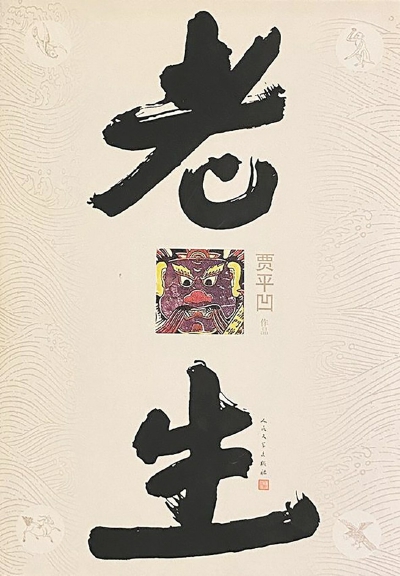
2014年

2018年
《暂坐》后记 □贾平凹
在我七十岁前,《暂坐》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酷暑才过,书稿刚完。字数是二十一万吧,整整写了两年,这比以往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它写了四遍。年纪大了,爱弹嫌,弹嫌别人,更弹嫌自己,总觉得这样写着不行,那样写着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
《暂坐》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对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它的小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二十一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
突然想写《暂坐》缘于我楼下的那个茶庄搬走了。茶庄在的那些年,我每日两次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后。喝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将就,我已经被培养成喝茶贵族了,茶庄却搬走了。人在身体好的时候并不觉得呼吸有多重要,一旦病了,才知道呼吸的重要,且一呼一吸是那样的紧迫,一刻不停。
茶庄卖着全城最好的茶,老板竟是一位女的,人长得漂亮,但从不施粉黛,装束和打扮也都很中性。我是从那时候,醒悟了中性的人往往是人中之凤。她还有一大群闺蜜,个个优游自尊,仪态高贵。我曾经纳闷:为什么男的没有,女的却有闺蜜呢?而且她的闺蜜还那么多?后来我也醒悟了,女的比男的有更多的心事,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女的,她们都需要倾诉,闺蜜就是来做倾诉的。那些闺蜜们隔三差五地来茶庄聚会,那是非常热闹和华丽的场面。这如一个模特在街上走,或许有人回头看,而十多个模特列队在街上走,那就满街注目。我是在茶庄看见了她和她的闺蜜,她们的美艳带着火焰,令你怯于走近,走近了,她们的笑声和连珠的妙语,又使你无法接应。
她们充满活力,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远自我。简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们就有多深的沟;你有云,云中有多少鸟,她们就有水,水中就有多少鱼。她们是一个世界。
现在,茶庄搬走了,不知是因经济下滑,还是强有力的反腐,作为奢侈品的高档茶已越来越难卖了,或者因房租太贵,员工的工资一再上涨,经营再也无法为继?而留给我的只是叹息,看茶碗在渴着,看蜡烛要烧死。
她们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暂坐》的文本。《暂坐》以一个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文所写:“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土垣,垣外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而菟丝女萝蔓延横生,日光漏叶莹如琉璃,叙述以气流布,凝聚为精则是结构之处。其中更有着陆以可的再生人父亲出现的奇异,有着冯迎幽灵萦绕的迷离,使这人间的人确实有了两种:人类和非人类。也时空转换着,一切都有了起伏不定、黑白无常的想象可能。
《暂坐》中仍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话有开会的,有报告的,有交代和叮咛,有诉说和争论,再就是说是非。
《暂坐》里虽然没有“我”,我就在茶庄之上,如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巢筑屋梁,万象在下。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事,说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们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的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在写这些说话的时候,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你一句,我一句,平铺直叙地下来,确实是有些笨了,没有那些刻意变异和荒诞,没有那些华丽的装饰和渲染,可能会有人翻读上几页便背过身去。但我偏要这样叙述。在这个年代,没有大的视野,没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小说已难以写下去。这道理每个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在让自己由土变洋,变得更现实主义。可越是了解现实主义就越了解超现实主义,越是了解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渡口。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这种迷茫、怀疑、叛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处理这些说话,一劲地平稳、笨着、憨着、涩着,拿捏得住,我觉得更显得肯定和有力量,也更能保持它长久的味道。尽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丰富自己,加强自己,来从事适合国情和自况的写作。视野决定着器量,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
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就试着来做撑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它的突破每每以失败为标志,俄罗斯的那个伊辛巴耶娃似乎从没有见好就收。
齐白石在他晚年的绘画中,落款总是要写上八十几岁或九十几岁,这是一种释然,还是一种炫耀?而《暂坐》之所以敢纯写一群女的,实在是我不自信使然。写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是她们在写我,这种矛盾和分裂随处可见。写到了最后,困扰我的是,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异后不再结婚?世上的事千变万化,而情感是不会变的吗?还是如看到的那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我就这么疑惑着,犹如这个城市在整个冬季和春季所弥漫的雾霾,满天空都是个谜团。
责任编辑:胡睿林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