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陕工网(029-87344649)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陕工网(029-8734464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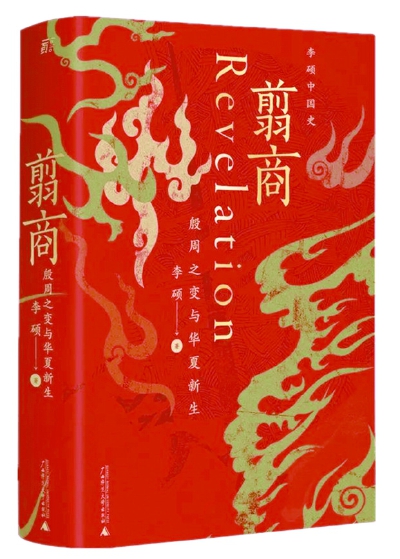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于殷周变革、周秦之变、唐宋转型这些名词一定不会陌生。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开篇即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作为周制的崇拜者,孔子曾慨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而历史文献对胜利者周朝的记录较多,却罕言及殷商制度,史家对商代认识的推进几乎全靠有限的甲骨卜辞和偶然发现的商代遗址。若不能与商代作对比,则周制的伟大便会大打折扣。时至今日人们对三千年前那场影响巨大的政治、文化变革仍然充满了陌生感。擅长讲故事的李硕用这部厚重又奇绝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为殷周之变提供了新的解释。
本书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商朝前史,第二部分是宏观的商朝史概览,第三部分则深描了周人的翦商史。后两部分是该书的主体。第一部分只有三章,看似是为商人的登场做铺垫,实则是用极少的笔墨举重若轻地回答了华夏族群何以从新石器时代迈入文明门槛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毫不亚于本书的主旨。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指出第一王朝夏朝的出现得益于两种技术的传播,一是水稻种植技术,二是冶铜技术。前者让人群的大规模定居成为可能,后者则为统治阶级提供神权与武力。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认为嵩山东部的新砦人是稻作技术北传的中介,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实则是河洛地区开始种植水稻的历史隐喻。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如许宏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作者通过“千粒重”这一农学标准弥补了考古工作中仅统计粮食颗粒的缺陷,由此他推断出稻米已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亦是洛阳盆地的主要作物。这段商代前史的梳理还透露出了作者的历史观,即技术、文化的交流是历史演变的根本动力。
把华夏文明完全带入青铜时代的商人从何处来?傅斯年先生认为商人出自东夷,此说在学界影响颇大,但很难从考古学上获得证据。李硕则从《诗经》《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的参商分离、王亥遇害于易水等故事出发,巧妙地提出了商人乃游牧民族的假说,他认为商人主要放牧水牛,进而又推定其部族主要活跃在黄河下游广阔的湿地沼泽地带,这是对商人东来说的有益补充。
接着,本书以众多商代考古成果为基础,勾勒出了商代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在此之前极少有学者敢做此尝试。作者先据郑州、偃师两处商城的规模以及两处庞大的商代早期仓储遗址,提出早商是商人利用青铜技术向外扩张的重要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已大大超过夏朝。此后引出全书最重要的线索即商人的人牲人祭现象。殷商的殉人习俗早已是学界共知,但作者通过细致的文笔对考古报告做了现场式的复原,这种勇敢的尝试为读者还原了甚至可以说是揭露了商代文明极为残酷的一面。
商人是青铜技术的发扬者,是庞大王朝的缔造者,还是文字的发明者,但以人献祭的习俗表明他们的精神仍未摆脱石器时代原始人群的荒蛮底色。远天近鬼而轻人,这或许就是商王朝的阿喀琉斯之踵。
如何为华夏古国去魅开蒙,完成这一重任的是周文王父子。然而文明的转向与精神的涤荡绝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牧野一战便以周代商那么简单。周人如何由弱变强,文王父子如何开启翦商大业,史书留下的线索并不多。作者通过解读《诗经·公刘》等篇目,指出周人早就与占据渭河的商朝有经济交流,后来周族领袖季历还与商朝联姻,周人一度成为商朝在西土的马前卒。在对翦商主谋周文王的刻画上,作者借鉴了高亨先生的方法,选择以《周易》卦辞为切入点,认为看似杂乱无章的卦辞其实反映的是文王对周遭事物的切身体验,如此便可通过对卦辞的解读来复原文王的翦商心态与翦商密谋。作者由此发现了伯邑考之死与人牲制度的联系,发现了文王曾在殷都密会姜尚,甚至通过“明夷”卦推断出箕子是文王的内应。这些推想十分大胆,但如作者所言,对易卦的钻研让文王明白了世界秩序并无常主。之后的故事,是大家都熟知的。□牛敬飞
责任编辑:白子璐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